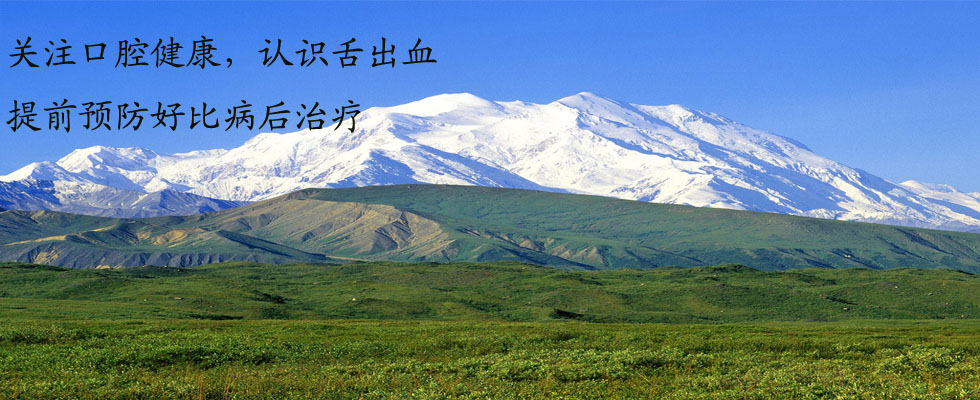■朱夏君内容摘要:昆曲唱腔在明清两代始终为研究之重心之一。20世纪以来,昆曲清唱之风日益兴盛,曲社林立,曲家辈出,昆曲演唱的技巧较之明清有了长足的进展,字面功夫愈益讲究,腔格愈益细腻多样。同时,清曲与剧曲也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与交融。其中,尤以三端最为引人注目:一是吴梅等关于唱腔的“学者化研究”;二是以《天韵杂谈》中的《昆曲唱法》为代表的“实践性”的唱腔研究;三是带有集成意义的“俞派唱腔”。总结过去一个世纪昆曲演唱中重要的观点与实践成就,能为今人研究与发扬昆曲唱腔的传统提供借鉴。关键词:昆曲 唱腔 吴梅 天韵社 俞派唱腔中图分类号:J80
文献标识码:A
文章编号:-X()03--08昆曲肇始于明代中期,以精美演唱之法独出曲坛。明清以来,魏良辅《曲律》、王骥德《曲律》、沈宠绥《度曲须知》、徐大椿《乐府传声》等度曲著作层出不穷,论及昆曲的辨音、咬字、曲情、宫调、习曲门径等内容(其宫调之内容,属于曲学音乐学的问题,本文“昆曲宫调”论及音律问题,在此不加赘述)。乾嘉以来,以秦腔和皮黄为代表的花部盛行剧坛,而昆曲则渐露衰弱之势,戏班和舞台扮演大为减少。至民国初年,虽昆曲搬演与创作几近衰微,但文人清唱之风仍颇为兴盛,大小曲社林立江南江北。曲坛曲家辈出,流派纷呈,以俞粟庐和红豆馆主溥侗分别为南北曲派之代表。昆曲演唱的技巧较之明清反而有了长足的进展,字面功夫愈益讲究,腔格愈益细腻多样。仅就润腔方式而言,俞粟庐《度曲刍言》、王季烈《螾庐曲谈》“论度曲”、吴梅《顾曲麈谈》相关章节、《六也曲谱》所附“南屏先生研究昆曲之唱法”、《怡志楼曲谱》所附“吟曲琐谈”对当时曲坛上流行的俗腔唱法进行归纳总结,其中俞派归结的俗腔唱法竟有16种之多。[1](P.-)另外一方面,昆曲演唱自清代中叶始有记录旋律之工尺谱,至民国初年,经曲家、曲师、艺人的大力推行,昆曲工尺谱开始大规模刊行出版,《六也曲谱初集》《昆曲粹成》《集成曲谱》《与众曲谱》《粟庐曲谱》等在民间流传。此时的工尺谱充分吸收了当时昆曲演唱中的经验与成果,板眼较为明晰(大多数标出小眼)、旋律较为细微,有的甚至标出气口和润强方式,便于学者参照习曲,对昆曲演唱艺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。明代以来流传于戏曲界之曲学,如果非有实际的唱曲的经验,则很难领悟体认。到民国初年,曲社中的教曲先生往往目不识丁。他们或按照前代口传心授的方式,或依照宫谱唱曲,既不明曲学源流,又不知音律。《顾曲麈谈》第三章“度曲”专论昆曲唱法,其云:“昔之习曲者,大抵淹雅博洽之士,其与词章之学,探索素深,平仄四声阴阳之际,辨别清晰,偶遇曲中词句,稍有不尽了然处,即能翻检而知之,故别字总不出之于口。今则学校教授,音韵废而不讲,学者年至弱冠,而与平仄且瞢如焉,遑论四声?遑论阴阳清浊乎?……近今曲师,率多目不识丁,每折底本,总有几十别字。学者即无家藏院本,足以校对,不过就文理之通否,略加改正,而好曲遂为俗工教坏矣。”[2](P.)前代曲学一派,在民初几乎成为绝学。吴梅先生有度曲的经验,擅吹笛唱曲,受到俞粟庐先生度曲治学的熏染与启发,故能排除当时曲学研究之杂芜,直接明清曲家之研究。《顾曲麈谈》从五音、四呼、四声、出字、收声、归韵、曲情七个方面论述度曲问题,其中辨音与咬字为吴氏度曲论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。在昆曲四声的唱法方面,吴梅结合古人的论述和自己的经验,云:“盖平声之音,自缓,自舒,自周,自正,自和,自静。若上声必有挑起之象,去声必有转送之象,入声之派入三声者,各随所派成音。……大抵阴平之腔必连续而清,歌时须一气呵成。阳平之腔,其工谱必有二音,其第一腔须略断,切不可连下第二腔,若既至第二腔,则又须一气接下,直至腔格交代清楚为止。……上声唱法,亦只在出字时分别。方开口时,须略似平声,字头半吐,即须向上一挑,方是上声正位。……去声唱法,总以有转送为主。何谓转送?盖出声时不即向高,渐渐泛上而回转本音,如椭圆之式是也。以北曲论,则用凡字音者,大半皆在去声。以南曲论,则凡属去声字,总皆于收音处略高一字,俗谓之豁。凡豁之一法,必在去声上用之。……入声唱法,以断为最宜。所谓断者,于字之第一腔,即凿断勿连,所以别于三声也。”[2](P.-)总结四声之腔格与歌唱法则,提出去声字的“豁腔”与入声字的“断腔”等唱法。吴梅度曲论内容上承袭沈宠绥《度曲须知》、徐大椿《乐府传声》等明清曲论的基本范式,加以自己的习曲心得融合而成。其所发之论,不出明清度曲论之堂奥,但在曲学衰微之时,吴梅熔铸旧学,参以感性的实际经验,在当时的曲坛起到了提纲挈领、振奋发扬的作用。王季烈《螾庐曲谈》第一章“论度曲”分“论七音笛色及板眼”、“论识字正音”、“论口法”、“论宾白”四个部分,内容基本上和《顾曲麈谈》“度曲”章相同。王氏“论口法”对字声腔格在内的多种昆曲俗腔口法,如豁腔、霍腔、断腔、掇腔、叠腔、擞腔等做了归纳。其云:“俗云‘去用豁、上用霍、入用断’。豁者,即送足其音,向高一带而即落下……霍者,即古时所谓顿音,适与豁相反,盖上声字固宜低起,然前一字如遇高腔及紧板时,曲情促急,不能过低,则初出稍高,转腔落低,而后再向上,亦肖上声字面。其转腔所落低音,即所谓顿音,欲其短不欲其长,与丢腔相仿,一出即须顿住,唱者于此将口一闭,即合顿音之唱法矣……至入声之断,则与上声之顿不同,上声之顿在转腔时,其出口近平声,不即断也,入声则一出口即断,极其短促,方肖入声本音耳。……口法中俗有所谓掇、叠、擞、霍者,霍腔前已论之。掇者,一腔中稍加顿逗,而唱作两腔。……叠者,将其腔重叠唱之,大都用之于腰板以下之长腔。……凡叠之前,宜稍断,以资透气,且使另起之腔,与前腔不相混,而益觉动听。擞者,摇曳其音之腔也。……掇、叠、擞三者相似,而掇之动作最为轻微,叠则较掇为沉着,擞则音杂而腔繁,其口法须动下颚,不仅用喉间之动作,方可使其音不改变。”[3](P.-)传统度曲研究一般以字声部分的论述比较多。魏良辅《曲律》中云:“曲有三绝:字清为一绝;腔纯为二绝;板正为三绝。”所以曲唱中的字问题,一直是第一要义。朱昆槐《昆曲清唱研究》中说:“历来论曲之书皆以大量篇幅讨论字音。但由于缺乏科学性的音乐符号,所能依据的只有历代韵书而已。但韵书只能说明归韵的问题,仍无法详细说明字音。”[4](P.)由于尊古守旧的原因,古代度曲论著虽然名目繁多,却只从书面说明昆曲中歌字的声韵归属,却很少北京治疗白癜风手术哪里最好北京治疗白癜风哪个医院看好